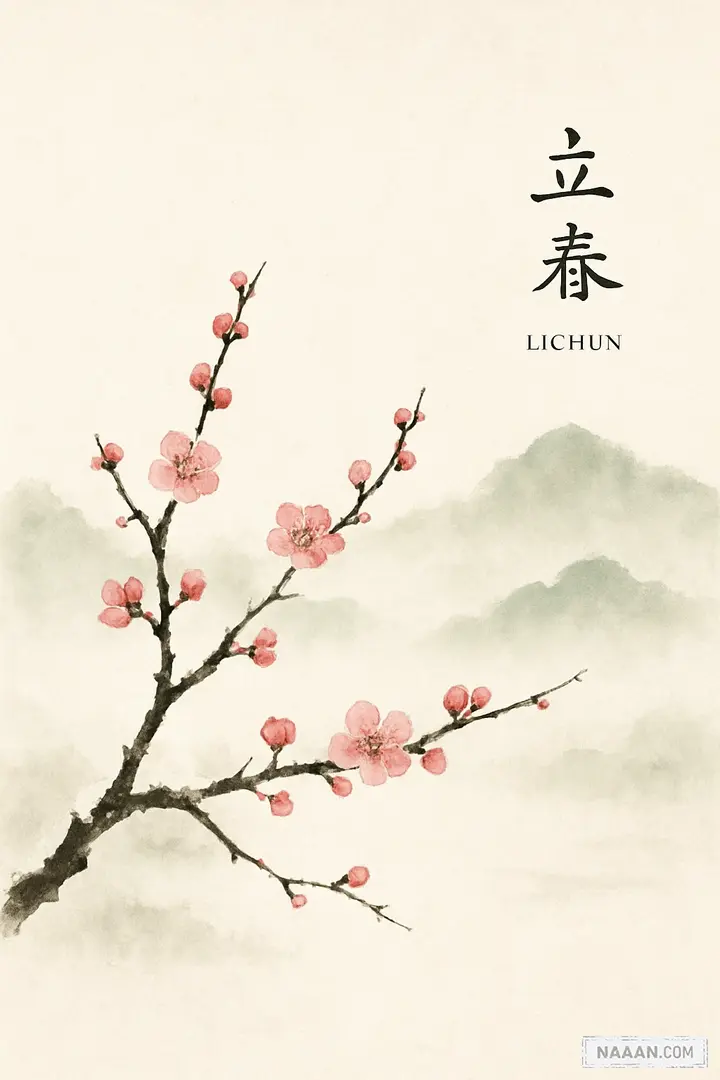L109_AI 时代的认知跃迁

今天是 2 月 21 日,也是农历年初五,一个重要的拜财神的日子。
所谓财神,不只是财富的象征,更是一种「流动」的状态。钱在流动,时间在流动,人也在流动。去远方,是为了看见更大的世界;回到原点,是为了更清醒地生活。
年味还没散,红包还在口袋里,家人已经开始讨论新一年的计划。新的一年,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身上。把精力投入到能够长期积累的方向里。
在这个睁眼就是AI新资讯、闭眼就是模型新评分的时代,焦虑感几乎成了产品人的底色。过去两年,我穿梭在亿级用户的AI特效与复杂的Agent探索之间,在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反馈中,我意识到:我们正处在一个生产力逻辑被彻底重构的转折点。